
天門山切壁直立,橫亙于甘谷縣城南,自古有冀城屏障之譽,說縣城屏風更為恰切。堪輿以天門山為甘谷主山,主一邑文運昌盛,雖玄乎了點,但造化弄物,自有其道理所在,要不,何以以一山而承全縣文脈,天嘉格局,果然妙不可言。甘谷有八景,首一景為“天門春曉”,可見天門山于甘谷地位之崇高。清鞏建豐《伏羌縣志》云:“天門春曉,邑南主山,三峰挺秀,若筆架然。春日芳草萋芊,山花絢爛,游人陟中峰,登眺覽勝。”
天門山俗稱筆架山,三峰并峙,一字排開,儼然筆架。中國多山,名山大川更是數(shù)不勝數(shù),但緊貼縣城,若城墻,“若筆架然”者,卻寥寥無幾。老天爺要偏袒一個地方,可謂用心良苦。天門山名天門,說高峻也高峻,但一定要在高峻二字上作文章,又未必見得。國內高度如此山者太多了,論高峻,天門山恐怕連入門的資格都沒有。天門山鶴立雞群,一枝獨秀,就在于她的“文”,在于她的“筆架”。有人說甘谷文風昌盛,從古代的科舉到今天的高考,學子踴躍,名士迭出,仿佛下餃子一樣,話是夸張了一點,卻也難掩實情。甘谷是教育大縣,也是教育強縣,大不大,強不強,當代教育還得用時間來檢驗,但明清科舉的輝煌,翰林、進士、舉人蟾宮折桂摩肩接踵,昔時風雅早已載諸志乘,傳于后世,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已不需要時間來檢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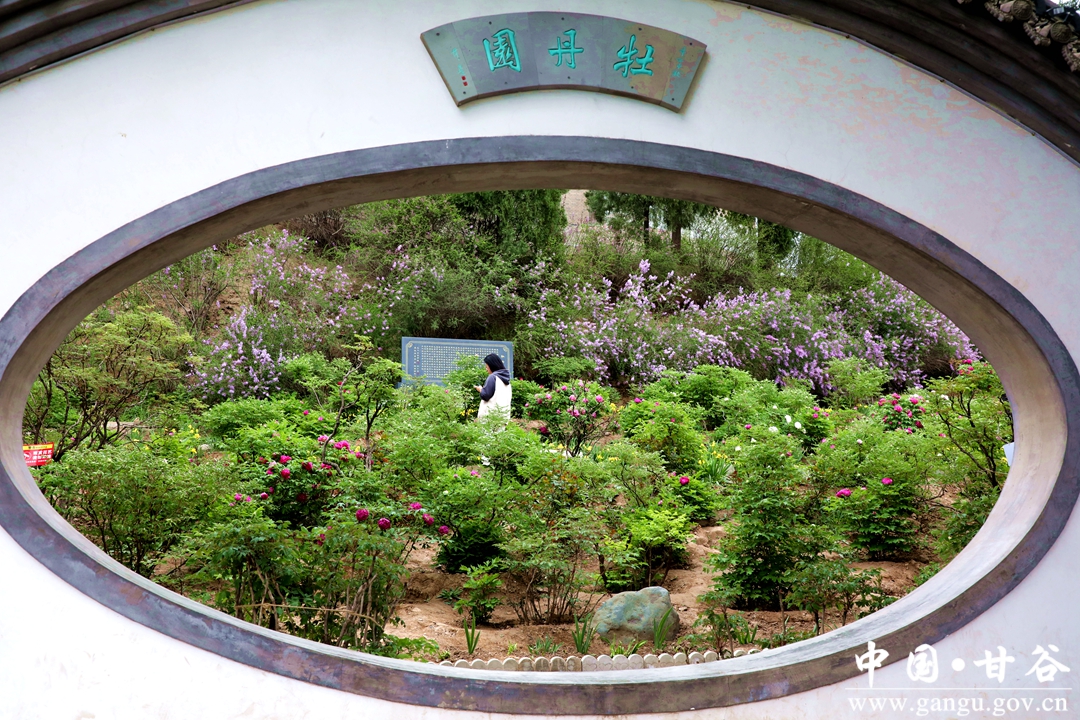
說到文,自然想到儒;說到儒,自然想到孔子,想到洙泗,想到杏壇和杏林。“孔子游乎緇緯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南華經(jīng)·雜篇·漁父》),孔子弟子三千,賢人七十有七,天水有秦祖、壤駟赤,甘谷有石作蜀。夫子授徒,常設壇杏樹之下,坐而論道,逮至今日,稱教育為“杏壇”者,概源于此。便有人問:“天門山既然名筆架,以文取勝,可有杏樹乎?”有,不僅有,而且十分茂盛。如果說文化是天門山的精神的話,杏樹和漫山開放的杏花便是天門山的衣飾。天門春曉,曉于何,曉于天門,曉于杏花。甘谷人計春,不以渭河兩岸依依楊柳計,而以天門山杏花怒放計。天門山杏花開了,甘谷人心目中真正的春天就到了。這種山和樹、文和杏的同氣相求,同聲相應,使天門山有了一種莫名的神秘和神奇。樹非人力而成,山非人力而起,筆架亦非人力杰構,大自然之妙,又豈人力能及。

天門山的杏樹不是一株一株,而是一片一片,只有在天門山,你才能知道什么叫花裹山。杏花開時,天門山被如云如霞,如霧如煙的杏花嚴嚴實實地包裹起來,從遠眺望,天門山儼然一朵盛開的蓮花,山巔天齊宮,儼然蓮蓬,那種神圣和高潔,真有種出塵入靜之感。幽幽微微、散散淡淡、依依裊裊的馨香,不僅包圍了人的口鼻,更包圍了人的心靈和精神。沒有沖天的香陣,卻也足以濯洗人們的心靈。耳邊,蜜蜂的嗡嚶之聲直擊耳鼓,如琴如瑟,似鳴似吟,有獨唱,有合唱,最多的還是交響,那么悅耳,天籟很難聽到,我想,所謂天籟不過如此罷了。置身音樂的韻流里,坐在花海的馥郁中,人不恍惚不由人,意不沉醉不由己。在拙作《杏園記》中,我以這樣的語言結尾:“是夜,見一蜂飛鳴于花海中,蜂是我乎?我是蜂乎?吾不能辨,問莊子,子曰:‘尚記得蝴蝶之事乎?’吾大頓,笑而不敢答,醒,乃南柯一夢也。”鐫刻作壁后,人皆贊收筆精妙,卻不知對我來說這其實是真實感受。所謂花不醉人人自醉,醉到深時,物我兩忘,天人合一。如此“沉醉不知歸路”者,我不是第一個,也絕不會是最后一個。

筆架、杏林、杏花,此中的聯(lián)系是什么,一時難以言明,茫然四顧,里許之內,來星塔、魁星閣、以及漣漪輕涌的柳湖,鴻儒鐘聚的學巷,騰蛟起鳳的一中,真有種“五百里滇池奔來眼底”之感。此時的天門山,既是真實的存在,又是精神的向心。文化是什么?文化就是天門,是從必然王國通向自由王國的最高境界。沒有文化,沒有文化自信,一切都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話似乎說遠了,但不可否認,天門山以文化自信給予甘谷的不僅是視覺的享受,更是靈魂的感召和精神的啟迪。

天門山是什么,是一年四季絕佳的去處,是從山下能仰望,從山巔能遠眺的理想的歸途。在以山作架,以筆賦形,以杏花鋪砌的勝境中,天門山將文化的無所不在,無所不及和奇幻莫測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登臨天門山,不僅僅是為了尋找什么,追尋什么,而是為了在現(xiàn)實和理想的交匯點上發(fā)現(xiàn)足以讓靈魂慰藉,讓精神超越的東西。這是山給予人的期望,是人之于山的感恩,是山和樹、杏和文無言的感悟與相恤,讓文化的根脈穿越千古,成為一場場漫天的杏花雨,淅淅瀝瀝,飄飄灑灑。
(來源:甘谷縣融媒體中心 轉載:康翠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