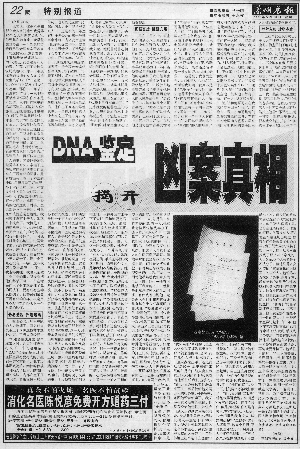
本報2002年5月14日刊發該案 《DNA鑒定揭開兇案真相》報道
10年前,發生在禮縣偏僻小山村的一樁滅門慘案震驚四野。獨守空房的年輕農婦阿平(化名)遭人奸殺,3個孩子也不幸遇難。案發后3個月,當地警方憑DNA鎖定犯罪嫌疑人王紅軍,同年8月王紅軍因犯強奸罪、故意殺人罪被判處死刑。
其后10年間,這起案件在三級法院之間起起落落,8份裁判書,3次被判極刑3次發回重審,警方也曾將29份物證樣品3上北京送公安部進行DNA鑒定。
驚天逆轉發生在兇犯第3次被處極刑提出無罪上訴后,省高院駁回上訴維持原判,并報請最高法核準死刑。死刑核準歷時2年,最終未獲通過被發回重審。案發10年后,省高院給了王紅軍起死回生的機會,改判其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但王紅軍感恩保命的同時仍對有罪判決堅決不服,繼續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無罪申訴。
為什么一個轟動一時的滅門慘案3個月告破卻進行了長達10年的馬拉松審判。而這場案件的庭審拉鋸戰也引發專業人士的深思。
案發 山村命案:DNA鑒定鎖定嫌犯
2002年1月5日,禮縣公安局接到報案:永興鄉友好村農婦阿平及其3個孩子被殺。案發現場慘不忍睹。阿平半裸,其身體多個部位均遭單刃銳器的反復刺切,3個孩子的頸部也均遭單刃銳器反復刺切。
法醫鑒定還顯示,被害人阿平死前有性行為。經過警方多方排查,先后兩次將28名嫌疑人提取血樣送往公安部進行“DNA”技術檢驗。檢驗結果證明與被害人同村的王木匠(王紅軍)有重大作案嫌疑。年僅24歲的王紅軍已經娶妻生子,平素言語不多為人老實,鄉鄰口碑不錯。村民為阿平辦喪其間,4口棺木還是王紅軍親手打造。王紅軍被抓獲,最終讓籠罩在當地的陰霾散去,當地群眾聞聽兇犯落網無不拍手稱快。多家媒體也對當地警方全力破獲此案競相刊發報道。
宣判 強奸殺人:一審被判處死刑
2002年4月30日,王紅軍因涉嫌故意殺人罪被逮捕。同年8月19日,省檢察院隴南分院以王紅軍涉嫌強奸罪、故意殺人罪提起公訴。
庭審中,檢察機關出示了公安部DNA鑒定報告書,證明被告人王紅軍當晚與被害人阿平有過性行為。另有從王紅軍家中提取、證實在案發現場其所穿沾有與其中3名被害人血型一致血跡的膠鞋的提取筆錄。值得一提的是,從阿平床上提取的衛生紙上提取物,經DNA鑒定還留存有另一人體液。而此人正是王紅軍嫉妒的“情敵”趙某。趙某接受警方調查時也承認其案發前確與阿平發生性關系。而根據體液遺留位置判定,趙某先于王紅軍與阿平發生性行為。
法院審理認為:王紅軍對頗具姿色的阿平垂涎已久,但一直未找到機會。案發當晚,王紅軍在村籃球場附近發現有人進入阿平家巷道并好久未見出來,便懷疑阿平“偷男人”。隨后王紅軍順著樹干爬上院墻溜進阿平家院內,貓身躲在北屋檐下窺視屋內活動,想以此要挾阿平就范,唯恐體格強壯的“情敵”對自己不利,其間,王紅軍還曾溜出大門回家拿上匕首返回。至凌晨,王紅軍待屋內男子離去便持刀入室,阿平為自保半推半就與其媾合。之后,當阿平憤稱要報案時,喪心病狂的王紅軍將阿平刺死。正當其用被子將阿平尸體蓋住準備離開時,發現上房的燈亮了,王紅軍又舉刀伸向了3個孩子。
2003年4月30日,隴南地區中院認定檢方指控犯罪事實成立,判決王紅軍犯強奸罪,判處有期徒刑10年,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兩罪并罰決定執行死刑。王紅軍受審時,當地法律援助中心一名律師為其辯護,但判決書中對辯護觀點僅僅摘錄“本案證據不足”6個字。
逆轉 歷時2年:高院重審改判死緩
2010年11月,最高法經過2年多的復核,作出不核準王紅軍死刑,撤銷終審裁定,發回重審的刑事裁定。同年8月29日,省高院重審后作出終審判決。這一次,王紅軍的命運發生逆轉。
雖然此次判決認定的事實與之前相同,但量刑由死刑變成了死緩。法院認定,王紅軍強奸婦女后有殺人滅口的行為已構成強奸罪、故意殺人罪,且犯罪情節特別惡劣,后果特別嚴重,依法應當嚴懲。但鑒于該案的具體情節,對王紅軍的量刑應當留有余地。
讓人吃驚的是,保住了命,王紅軍仍不買賬。王紅軍告訴家人,雖然自己性命暫且保住,以此感謝最高法的同時也很失望,因為法院最終還是沒能還其一個清白。看守所內羈押10載,王紅軍為自己因為生活中的不檢點招致殺身之禍,妻離子散而深深后悔和自責。
反復 堅稱無罪:再向最高法院申訴
2012年年初,王紅軍向最高法遞交了申訴書。王紅軍的代理律師,甘肅謝志剛律師事務所律師謝志剛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若本案的真正兇手就是王紅軍,為何連殺4人,卻僅被判處死緩,對死者不公。若證據不足,更就不能認定王紅軍就是本案的真兇,為何不依“疑罪從無”的司法原則判其無罪。真正的殺人兇手究竟是誰,是否至今仍在逍遙法外?謝志剛也表示,他對王紅軍的申訴不作樂觀預期。
評析 不斷重審暴露刑訴制度缺陷和司法難點
對于這起罕見的3次發回重審、兩級法院4次判決,量刑從死刑到死緩的案件,我省刑辯第一人,省律協副會長刑事專業委員會主任,甘肅東方人律師事務所主任律師尚倫生表示,這個案件反映了刑事訴訟制度的某些缺陷和在實際操作中存在的問題。
尚倫生認為,我國《刑事訴訟法》對案件發回重審的次數并無規定,但兩高聯合公安部發布的《關于嚴格執行刑事訴訟法切實糾防超期羈押的通知》明確規定,“第二審人民法院經過審理,對于事實不清或者證據不足的案件,只能一次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這個規定具有司法解釋的性質,對于人民法院是有約束力的,應當嚴格執行。王紅軍的案子多次重審的理由是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但二審法院以事實不清及證據不足的理由發回重審,檢察院重新調查事實,一審法院重新組成合議庭進行審理的判決仍舊一次次被認定為事實不清及證據不足。
該案所暴露出的問題是,我國還沒有真正建立起疑罪處理的機制。雖然最高人民法院一直強調“有罪依法追究,無罪堅決放人”,但司法實踐中缺乏可操作性。于是,法院一般采取的處理辦法往往是“疑罪從輕”而非“疑罪從無”。同時,司法機關面臨著社會輿論和維穩壓力,還要面對被告人、被害人等方面的壓力。這些因素都制約著司法機關的裁判,司法工作同樣需要社會的理解和支持。
尚倫生介紹,為避免案件在一二審法院之間反復“踢皮球”,將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發回重審只限一次。
本報記者 郭玉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