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8月上旬,旅居天津的天水籍青年作家秦嶺(何彥杰)西部采風途經我市,并應邀參加了我市舉辦的女媧文化研討會等一系列文化、文學交流活動。《天水日報》記者丹霞就秦嶺最近問世的兩部小說集《繡花鞋墊》《紅蜻蜓》進行了采訪。這兩部小說集收入了作者近年來創作的部分農村題材和官場題材小說,其中多部在全國、期刊和天津市獲獎。現將丹霞和秦嶺的文學對話摘要如下,以滿足天水讀者的愿望。
布谷鳥在海濱自由歌唱
——與天水籍青年作家秦嶺(何彥杰)談其小說創作與生活
丹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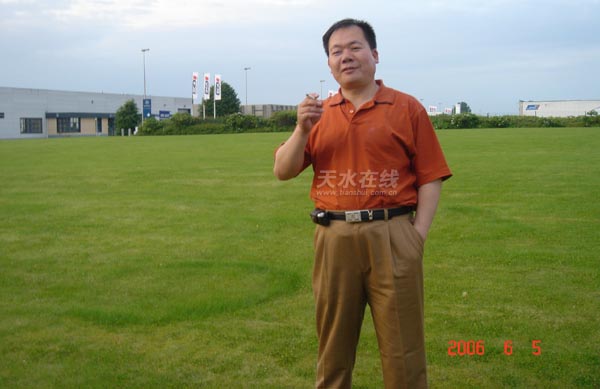
丹霞:你好!首先作為家鄉人對你在中國文壇的迅速竄紅(請允許我用這個字眼)與你的《繡花鞋墊》、《紅蜻蜓》兩本小說集的出版表示真心的祝賀。
秦嶺:謝謝!我也借此機會向多年來關注、支持我的天水各界的新老朋友表示誠摯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謝!《繡花鞋墊》《紅蜻蜓》兩本書篩選并收入了最近四年在《鐘山》《長城》《紅巖》《北京文學》《天津文學》《長江文藝》等期刊發表的19部中短篇,算是對自己近期小說創作的階段性小結吧。
丹霞:在上面我用了迅猛竄紅這個字眼,來形容你在小說創作方面態勢,因為在我的感覺中,你這幾年的小說創作是循序漸進的,但又是非常迅猛的,以至于迅猛到三四年之內就在國內的文壇上獨顯崢嶸,耀人眼目,但又有點相似。能具體談談你在天津這幾年的文學創作與發展情況嗎?
秦嶺:對于最近以來國內媒體對我的關注,我有著清醒的認識,與全國和天水的一些優秀作家比,我需要努力的地方還很多。我是2000年重新開始小說創作的,在這之前由于先后在甘、津兩地黨政機關從事繁忙的文秘、組織人事等工作,放棄創作達10年之久。所發表的170多萬字的作品,大半是近年寫的。有四個標志對我來說很重要,其一是從2001年開始發表了一系列農村教育題材的小說,其中中篇《繡花鞋墊》登上2003年下半年中國最佳小說排行榜,評論界認為“把這塊蛋糕做出了別樣的味道”。其二是四年來的幾次獲獎,其中《難言之隱》《年輕的朋友來相會》《碎裂在2005年的瓦片》等獲得期刊優秀小說獎、2003年度、2005年度天津市文化杯中篇小說一等獎、中國梁斌文學獎等。其三是2002年被評選為天津市文學新星,用作協領導的玩笑話說“秦嶺像一只在甘肅蟄伏多年的狼似的突然竄進了天津文壇”。其四是被天津市文學院聘為簽約作家,有幸成為17名簽約作家團隊中的一員。這四個標志改變了我對文學一慣迷惘、躲閃、矜持的怯畏心態。用《北京娛樂報》記者的話說,就是“這段時期,秦嶺就像一個睡眼松惺的騎手,在懵懂中形成了自然的狂奔狀態,由于懵懂,他竟然忽略了去享受本已降臨的愉悅。”我想,所謂“竄進來”,離不開力量的積蓄。文學一如吃飯,第一口飯菜未必能馬上填飽肚子,卻是最值得回味的,如果沒有20多年前的1985年在天水農村上初中時發表第一篇散文和1988年加入天水作協等并非遙遠的經歷,我文學的肚子恐怕早就被物欲世界的平庸和世俗填充了。
丹霞:你的小說除了在國內的名刊刊登,許多小說還被《新華文摘》《小說選刊》《小說月報》《中篇小說選刊》《中篇小說月報》《作品與爭鳴》等中國著名選刊選載,有些小說還被收入《2001年中國優秀短篇小說精選》《中國鄉村小說選》《中國官場小說選》《2003年下半年中國最佳小說排行榜佳作集》等選本,無論是中、長篇還是短篇,都充分證明了你小說所具有的雅俗共賞的藝術效果,使嚴肅理性、承載著深度社會意義的文學作品被專家和讀者同時認可,作為創作者,你有什么樣的“秘訣”?
秦嶺:套用某政治家言,在創作上我屬于摸著石頭過河的那種,因此在這里談秘訣有些底氣不足,但是摸石頭的那種粗粗拉拉的感受還是有的。在京津地區一些文學活動的發言中,我始終說我有兩個榮幸,一個是近年來文學回歸現實的大氣候為我揚長避短提供了可能,二是在黨政機關先后從事的文秘、人事、督查等不同崗位成全了我審視社會的角度。有一點我從骨子里始終堅守著,這大概和我的創作個性有關,那就是我只認準文學創作的基本規律和紀律,無意在時下亂花迷眼的技巧上去追風逐浪,也很少去刻意營造完整的故事,而是有意不斷變幻視角,注重采擷生活碎片的反光,收集到主題的拼盤中來進行寫實敘事。有些評論家給我小說的定義是 “秦嶺的小說最大的技巧就是沒有迷信別人的技巧。”這使我體味到了拒絕盲從甩開膀子走路的快意。最近我搜集了一些關于我小說的評論,特別是研讀了《作品與爭鳴》等期刊上討論我小說的理論文章,使我從外部看到了我走路的姿態和模樣。既然尚在摸索期,我倒真的渴望找到萬能的秘訣,那一定會使我聰明和靈巧起來。
丹霞:對你的小說,許多大家、名家在《文藝報》《作品與爭鳴》《中篇小說選刊》《中國文化報》《中華讀書報》《天津日報》等報刊中作過各種各樣的佳評,今天,我只想從家鄉人這樣一個視角談一點讀后感受。首先談到的還是題材,就你小說創作的題材而言,農村和城市,構成了你目前小說題材的兩大支點,這從你這兩本集子的書名也能反映出來,這是否與你的出生地和現居地——天水和天津的生活有關?
秦嶺:應該說是有關系的。我的小說中對中國農村社會的反映,很大程度上源于對故鄉天水農村表象的深刻記憶和參加工作后對農村社會普遍意義的思考。有意思的是,您提到的《文藝報》《作品與爭鳴》等報刊上評論我的文章,針對的基本都是我的鄉村題材小說,如《坡上的莓子紅了沒》《硌牙的沙子》《碎裂在2005年的瓦片》《鄉村教師》《棄嬰》等,這些小說發酵的土壤,就在天水的西河、渭河之畔。而天津作為我的第二故鄉,她直轄市的魅力使我真正觸摸到了城市的呼吸,10多年來,我思考和工作的觸角延伸到了這個城市的許多領域,我從這里出發,先后涉足了歐洲、東南亞的一些國家和城市。天津使我對世界的認識更為直觀和理性,我想,我下一步會更為冷靜地體味這個城市的生命脈搏和人文精神。其實天津周邊也遍布著美麗的鄉村,這里的鄉村比天水的鄉村要富饒得多,湖泊蕩舟,沙鷗漫舞,但那只是我帶著妻子和兒子度假的美妙去處,卻很少走進我的鄉村小說,我藝術上的鄉村生活始終黏糊在天水的崖畔上,馓飯似的,兼有酸菜和玉米的醉人芬芳。
丹霞:如果從文學的心靈關照而言,我感覺,你的小說,折射的是你心靈中的兩種情態,反思和體驗,一種是對故鄉生活尤其是農村教師生存與生活狀況的思考,比如你最早引起國內文壇注目的《繡花鞋墊》以及其后同類題材的《燒水做飯的女人》等,都屬于這個范疇,另一種則是作為一個都市旅居者對于城市中各種繽紛尤其是都市官場生活的體驗,如中篇《難言之隱》《打字員蓋春風的感情史》《年輕的朋友來相會》等,是這樣的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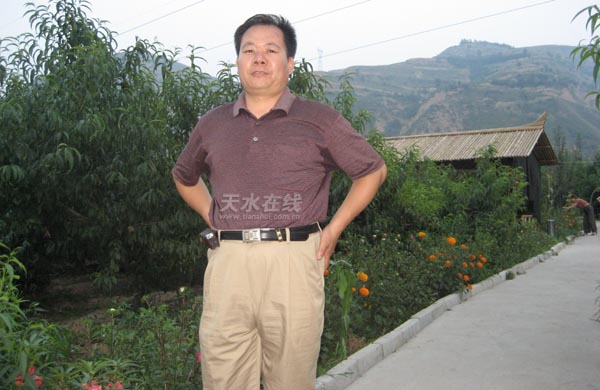
秦嶺:最初選擇鄉村教師題材,大概與我在天津接受高等教育有關,并不遙遠的關于鄉村教育的記憶與發達的直轄市教育在我腦海里形成了強烈的對比,特別是后來應邀在北京、天津的一些富麗堂皇的大學交流小說創作,我對卑微的鄉村教師這一特殊群體的思考更加趨于冷靜,這使我的視角執拗地停留在那些中國農村教育的主要承載者和文明的傳播者身上,走進了他們不堪的生活、生存狀態之中。至于官場小說,對我來說是個順理成章的收獲。身處官場核心部門,每天如果不是步履匆匆地在上級機關和基層部門之間穿梭,那么就是在撰寫調研文章,八小時之內用文學的思維審視官場的機會并不多,精力全部用在黨務和政務工作中了,從某種角度也可以看到我當時的精神面貌,我曾有意不寫官場的,但終于沒有管住電腦鍵盤上恣意彈跳的指頭,一口氣發表了20多個官場題材的中短篇,出版社的編輯是這樣概括這些小說的:“在體制、權術、倫理的背后探幽人性碎片,并按人性脈絡拾掇起來,構成了一幅幅妙趣橫生、幽默風趣的漫畫。”這些溢美之詞,我權當抬舉之言,事實上折射了我的官場體驗和文學思考。我認為,官場像一個無法謝幕的特殊劇場,我很慶幸自己既當演員又當觀眾的日子,使我用文化的心態咀嚼著官場的真味。官場是幽默生活與幽默藝術的富礦,而出于工作需要發表的40多萬字的社科類論文,又從理論上增強了我體味官場生活的嗅覺,不斷豐富著我的思考,不過在我近期的創作計劃中,官場小說并非我的重點,我將繼續讓我文學的視角以犁鏵的姿態,在鄉村的土壤中破土穿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