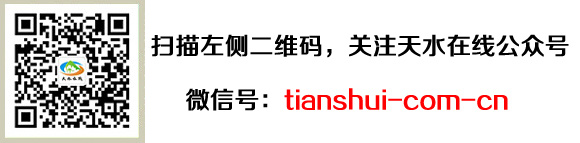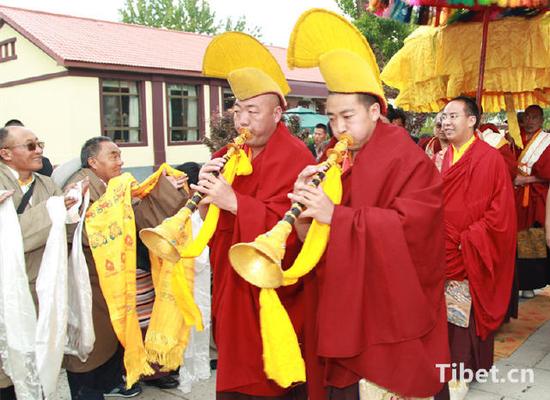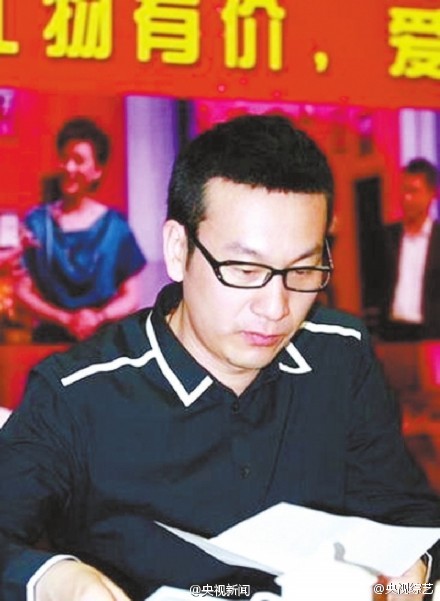���������塱
�A�̈��L�M��/�D

���� ���������S��ɢ��ѷ� ������ɢ�������ϴ��ƾ�ƿ
�����҇�ÿ���r(n��ng)����������1.2�|��
����ȫ��4�f���l(xi��ng)�(zh��n)����60�f��������
�����S���]�Эh(hu��n)�����A�Oʩ
�����е�߀̎��������Ȼ�ѷŠ�B(t��i)
��������������h(hu��n)���ա��A�̈�ӛ�ߌ�Ŀ��Ͷ�����l(xi��ng)���������}�ϡ�
��������3�£����ҭh(hu��n)�������Lꐼ���ָ�����҇��ĭh(hu��n)����Ⱦ�����M��һ������ɽ���l(xi��ng)���������I(y��)��Ⱦ���ɖ|�����������D(zhu��n)�ơ��ɳ������r(n��ng)���D(zhu��n)�ơ��l(xi��ng)������(j��ng)�����������}�����؉��ȣ���ɫ��Ⱦ���h(hu��n)���Ɖģ��ˮ��ȫ����������w��������
�����l(xi��ng)�������������ѽ�(j��ng)���˿̲��ݾ��ĵز���
�����@��һ������������ɽ��
������ɽ�����߰�ʮ�ף����s�������ף��Ŀ��и���q��һ�l��ɫ�ľ��࣬�����o�ɑ������M�ӹȣ�������ԭ�������@���һƬ�Gɫ�������܇����]�И�ľ��Ҳ�r���s�ݣ�ֻ�Џ����ij��⡢�w������������Լ��o��(sh��)��ω�ڿ��м��w�̔_��
�����@�����Ǭ�hĮ�Șġ����^һĻ�����ڮ�?sh��)���ӛ���У��@���я������������׃������������䌍������ɽ���Ժ����Σ��˂��o������
�����������Ў�ʮ���ˣ�ÿ�춼�Ў�ʮ܇����������Ǭ�hĮ����^(q��)�ď���̫̫�f�������ÿ���ߵ���߅�������е�����µûš�
�������������ˡ�������
�����ܶஔ?sh��)��˶�߀ӛ�ã�����ǰ��һλ�������ӱ��@������ɽ���ɡ�
�����������3���ˣ�һ����ʮ���q���е���ɽ�ϓ���������������������ס�ˣ����L�r�g�]�ҵ��ˡ���Į�Ș�߅һλ�I�����ӻؑ����f�����£���������ɽ�ϓ�������ʰ�����y�^���f���ǂ������������Ǹ������f��ģ������F���°l(f��)ǰһֱ�����@��ʰ���^�
����������ɽһ��(c��)��ȥ���¶�����������ʮ�ȣ��̎���s�߰�ʮ�ȣ�������Ҋ������]���e�ı��o��ʩ��Ҫ�����@ô���ĵط���ʰ����ȡ������Ҳ�H�����ס�
������һ����ǰ��һ�����g��ľͻ���ȥ�ˣ��ҺÛ]��ʲô�¡���������ɽ��ɽ픡���һλ����ñ��ʰ�����f�����@Щ������Խ��Խ�࣬ɢ�l(f��)�Ě�ζҲԽ��Խ���ς���С�r����Ҫ�Dz��ߣ����ܰ���Ѭ������
��������һ�l��һ�v�v����܇܈���ġ��۷x������С·�����L�Mӛ�߰l(f��)�F(xi��n)��̎������ɽλ�ã����H����ӹ��������ӣ��������܇��r(n��ng)��Uɢ��څ�ݣ��h(hu��n)����ܣ����o�˾�סҲ�o·���^�����؈D�@ʾ�����xԓ����ɽ�|���s6�����һ�������ĹŴ����꣬�����ϣ���һ������ˮ�졣
����һλ�������f��Į�Ș��µĊA������ǰ����ˮ�ģ�ֲ��Ҳ��ïʢ����ɫ����������������ˮ��ȡ�Ժ��У�������ӵ��]ˮ�ˣ����������һ܇һ܇�\���^�������ڜ��Խ��Խ�ࣻ������꣬�����˂�������ˮƽԽ��Խ�ã���������Ҳһ���Ӱ������ѳ�Û�ˎ�ʮ����
�����������f��ˮҲ�Բ����ˡ���ס��Į����^(q��)��һλ���˸��V�A�̈�ӛ�ߣ��܇�һЩ����ĵ���ˮҲ�]�����ˣ�����������o�����ԁ�ˮ��
�������ڳ������������r�е�����ɽ�܇�ȥ�ģ���������ˣ�ÿ�괺�ĹΖ|���L�ĕr������ɽ��ɢ�l(f��)�����Đ�����Ȼ���ԏ�����(sh��)������l(xi��ng)�塣
�������Еr����ɽ߀����ȼ��ɢ�l(f��)����ζ���]�L�r�����L�r�g�����yɢ�_�����Ю�?sh��)��˽�B����һ�궬�죬����ɽһ̎��ȼ��ʮ�춼�]Ϩ�磬ֱ������һ��ѩ��
������(j��)Ϥ��Ǭ�h�h���ծa(ch��n)���������s�����ه���һλ��Ը¶�����ĭh(hu��n)�l(w��i)�����v��ÿ������2�r�ͮ���7�r������������܇���ռ������ؽ���ߵĸ�������������@Щ�������֑�ԓ������Į�Ș�������������?sh��)صĭh(hu��n)�l(w��i)�����ˆT¶�������@�Ǭ�h߀��һ����������������������x�h���^�h���ܴ�һ���������ŵ������@�
�������ϣ������������h��ֹĮ�Ș��@̎����ɽ����Ǭ�h���S���ϡ�ע���(zh��n)������(zh��n)�ȶ�̎���(zh��n)�l(xi��ng)�壬�A�̈�ӛ�߰l(f��)�F(xi��n)�������������S��ɢ�䡢�ѷ��ڴ�߅�ĬF(xi��n)�����@Щ�ɰ�ɫ���������U�f����ƿ���(g��u)�ɵ��������ܶ�����˾��Ҋ�T�ˡ���
����������ɢ�������ϴ����ƾ�ƿ
�����ھ�Ǭ�h�sһ�ٹ�����R�����S���l(xi��ng)�������ʬF(xi��n)����һ������
���������S���k���x�F���sһ�ٶ����h���~�ұ����ڣ���һƬ����ƽ���Sɫ�؉K������ԓ�؉K߅���@�F(xi��n)���������������t�f�����@Ƭ�S�����棬����һ����������������@�������������mȻ��������һ���������������K�@����e��ǧƽ������������Ȼ߀�����|���һ���Ӝ������죬�����ڜϵIJ�ͬλ�ã����DZ����W���ˡ�һ�㣬Ҳ��̎�e������С���ȵ������ѡ�
�����@Щ�������������ԭ����Ք���һ���ֵĚ�ζ����վ����������������Ȼ���������������������N�������ϻ��s��һ��ij�ζ��
�����������|Ŀ�@�ĵ��ǣ��ڴ���ԵĴ�Ƭ�����ɢ������N�ɫ�Ͳ��|(zh��)�����ϴ�����ɫ����ĭ������ľ�ƿ�����l(f��)ù��ʳ��ȡ������@Щ���s����ɫ���������������֪�����ո�r�ǺηN���飿
���������~�ұ������У���Ȼ���Կ���һЩ��ڡ���߅������S���������������������β����@Щ�������ɽy(t��ng)һ�ĭh(hu��n)�l(w��i)܇�v̎��r������ֻ��ЦЦ���u�^���Z��
�����ڽӽ��Dž^(q��)����ʼ����|������һ̎����������ɢ�أ����ڴ�̎����·߅���־���լ���h������δ���\�ߵ�����ɢ�����⣬����Ѭ�졣��(j��)����ë�Ҵ��һλ�����B����ǰ�@�ﲢ�]���������������֪��ô�������_ʼ���@��A��������������һ������܇��ľ������Ѳ�����_��
����ͬ�ӵ����������������Ļ��@����ʮ�����ۡ���ԓ��山��·߅��һ��ռ�ؽ�����ƽ����������������(j��)�Q�Ѵ��ڔ�(sh��)��֮�ã����治���б��ӵ���ƤЬ����ɳ�l(f��)��߀�ЏU�����RͰ����(sh��)�Ѹ���׃�|(zh��)�����ӡ�����һ�����f��������ǰ���fҪÿ��ÿ�������ռ����������ģ��������֪��ô��ȫ�ѵ����@Ƭ�յ��ϣ�һ�����죬�����B�T�������_��
��������ڑ��h��̫·��߅�IJ����(zh��n)���ϴ壬����һ�����R���������������ľ��ȡ���ԓ�����Ѓɂ���ɳ�ӣ�һ���s�����һ�Ӵ���һ���а낀������Ӄ�(n��i)��δ��������M������̎߀�e���G��ɫ����ˮ��ÿ�Џ��L���^����ɫ���{ɫ�ľ������͕������h�ӣ������f������������ѷe�˺Î����ˣ��]�˹ܣ�һЩ���p�����K����Ը���ڴ������
�����������y�����y�����ܵ�߀���L���^(q��)���ٽ��k˾�R��ď��մ�����ԓ���ڣ���һ̎����ʮƽ���������_�����������ѽ�(j��ng)��M���F(xi��n)�Ѷѵ����棬���߰����˶��]�˹ܡ������f����ǰ�X���Ђ������_�����ӵ��l(w��i)���h(hu��n)������һЩ�����F(xi��n)�ڿ��������������Oʩ��Ҫ�Ǜ]�Ќ��˹�����߀��һ�ӕ���Ⱦ�h(hu��n)���������������H���F(xi��n)�ڴ����܇���߀���F(xi��n)���^��Ƨ�o�Ĵ��⡣���~��··����(sh��)����һ̎�S��zַ�܇���ӛ�߾Ϳ�����һ��ъA�s��������ƿ�����ϴ��͏U�f������ľ�弈м�������������F(xi��n)�ڔ�(sh��)�ѽ��������ԣ���·�ڵ��zַ��ַ���Ͽ�ȥ������ٲ��M�ж��ƣ��zַ��(n��i)�Ĵ�Ƭ�ط����ݱ،����������ռ��(j��)��
�����r(n��ng)��������ô��߀�ǂ��y�}
���������������������Щ���S��G�����ڽ�ɽ�ĺӵ��У��������⒁�S�z����������Ҳ�o�h(hu��n)��������С�ĉ�����6��4�����磬���؎X̫ƽ���У�ӛ�߰l(f��)�F(xi��n)�ӵ�߅���˟������z���²��پ����������ƿ�����Щ���L��������ϣ��еĄt�h�ں��
����������������F(xi��n)�����кܺõĹ��������r(n��ng)�����������ԓ��ô�ܣ�߀�ǂ��y�}���������S��zַ���h����ˮ������_ijС�r�����ڴ���L����ڳ������ʾ��Ŀǰ���������������̎����ʮ�������r(n��ng)��ͽ�ɽ�^(q��)߀���^�S��ͻ�y�������ڭh(hu��n)�l(w��i)�Oʩ������r�£��˂��S��G��������������r�ѽ�(j��ng)�γ����T��������ô��h(hu��n)�l(w��i)�������h(hu��n)���l(w��i)�����o���R��ÿλ�������������ǂ�ؽ����Q�Ć��}��
������(j��)�˽⣬�҇�ÿ����r(n��ng)������������1.2�|�������Ұl(f��)չ�c��(zh��n)���о�Ժ2015��l(f��)���ġ��҇�������������������r�u����桷�@ʾ������ݠ�^(q��)���r(n��ng)�岿�����ڃ�(n��i)���������������o����̎���ʃH��62.02%�������A��W�h(hu��n)���WԺ�ṩ�Ĕ�(sh��)��(j��)�t���f������ȫ��4�f���l(xi��ng)�(zh��n)����60�f���������У����S��]�Эh(hu��n)�����A�Oʩ���е�߀̎����ԭʼ��������Ȼ�ѷŠ�B(t��i)��
����2016��3�£����ҭh(hu��n)�������Lꐼ���ָ�����҇��ĭh(hu��n)����Ⱦ�����M��һ������ɽ���l(xi��ng)���������I(y��)��Ⱦ���ɖ|�����������D(zhu��n)�ơ��ɳ������r(n��ng)���D(zhu��n)�ƣ��r(n��ng)�����ܭh(hu��n)����Ⱦ�ı����������������{(di��o)���@ʾ�������r(n��ng)�����������ò������r̎�����O�a(ch��n)����������ˮԴ�صĶ�����Ⱦ�����⣬�����ȾҲ�ڼӄ��r(n��ng)��h(hu��n)�������R�ć���̎������һЩ���Ќ��������������������\���ǽ��l(xi��ng)��^(q��)��ʹ�úܶ��r(n��ng)����˳��еġ�����̎��������������ġ��������ǡ�׃���ˡ��������塱��
�����@Ȼ���r(n��ng)����������̎���Ѳ���һ��һ�(zh��n)�Ć��}��2015���������1̖�ļ��״Ό��롰�r(n��ng)���������������h��ʮ�ˌ�����ȫ��ͨ�^�ġ�ʮ���塱Ҏ(gu��)��Ҳ�����Ҫ���_չ�r(n��ng)���˾ӭh(hu��n)�������Єӡ���ȥ��11�£�ס������ʮ���T(li��n)�ϰl(f��)����ȫ�����M�r(n��ng)������������ָ����Ҋ��������ʹ���r(n��ng)���������������õ��O���Ƅӡ�
�������r(n��ng)����h(hu��n)�l(w��i)���������һλ��Ը¶�����Ļ�����ʿ���Y(ji��)�r(n��ng)����������̎����������������y��һ���r(n��ng)����������̎��]�нy(t��ng)һ�Ľ�(j��ng)�M���ϣ�̎���Oʩ��̎����������ƌW�������������ռ����������\ȱ�����T�ˆT�����Ǵ�����l(w��i)���h(hu��n)�����R��ܶ�ª����δȥ�������õ����T��δ�������������f������ԣ�Ĵ�����������̎�����һЩ������ԣ�Ĵ��Ӿͱ��^��y����
�����Ќ����J�飬��ǰ�҇�С���(zh��n)��δ���������ա��͡�̎�wϵ�������ռ���̎���ʵ͡���ˣ����Ӵ����r(n��ng)��^(q��)����������̎��Ͷ�룬���ӭh(hu��n)���Oʩ������Pϵ��ʹ���r(n��ng)��^(q��)�������õ���Ч�ռ���̎�����Ķ�����Ŀǰ�ij��l(xi��ng)��������������
����һ�����ӵ�����ȥ��
�����������]̎�� ��������ˡ�
�������؎X�h(hu��n)ɽһ������һ̎��ɫ�컣��������˵�С���f�������h�����塣ԓ���������ɮȡ��(j��ng)�Ă��f����(j��)�Q�������@���һ�l����������ɮ�����T���챻������ǣ�����С���R������˂���ס�ڴˣ������˰����塣�@��һ�������؎X�_�£��h(hu��n)����(y��u)�������쪚��Ĵ��f���l���뵽���sһֱ�����е������������_����
�������������ɴ���ج��
������ԓ����ϣ�һ̎��(sh��)��ƽ���������������ڼ�������У���Ȼɢ�l(f��)���ɹɐ�����
�������@���ط���ǰ�ǂ��~�����~���U����ͳ��˺����F(xi��n)�ڣ��A�������������ѿ쌢����M�ˡ���ס�ھ�����������100�Ĵ����Z������V�A�̈�ӛ�ߣ���(j��ng)�^����Ķѷe��������|߅��һ̎�ط�߀�ɵ��⣬��߅���ѽ�(j��ng)�ӽ������ˡ�
�����mȻ��߅�����������M����һ�������������������д��A���Ĵ�������������U���
������ȥ�����������ܶ࣬���������϶�˯�����X�����Z�����f������2010�꣬���������^һ�μ����ռ�ÿ��ÿ�������������Єӣ����ҽoÿ�Ҷ��l(f��)��һ���Á��ռ�����������Ͱ���������Ͱ�ֶ��������������ˡ�
�����mȻ�������������Ǵ����ڴ��У������x��ԓ��|�潛(j��ng)�^�ĸʺӣ�ֱ������200�ס�
�����ܶ������Մ�������@���������r����������ü�^��������������Ҫ�댢������Ū�ߣ��������¡�
�����S����������ª��
�������H�ϣ������@��������ᔡ�����������ԓ����S̎��Ҋ�������S��G�����������ڴ���߅�����߅��ɢ����ʮ�ׂ���ɫ�ľ���������һ̎���ڣ���������ʮ���ߵ��������ѷdz��@�ۡ�
�����ڴ�ڵ�Сʯ���£�һ�lϪ��������|�R��ʺӣ����Ę�����ȥ��С�ӵĺ������ѱ鲼�����������u���������ƿ���l(w��i)���������������r(n��ng)ˎƿ�ȵȣ��ɞ��c���ӘO���f(xi��)�{(di��o)��һĻ��
�������@���Ǵ����Լ��ҵ��������]̎������������ˡ���һλ�����f���l(f��)����Ͱ��һ��ӣ�ÿ��ÿ������������߀�������أ����]�����ˣ���Ҿ��S��G�ˡ�����������Σ�����@λ�����ʾ���Ĵ_��Ӱ��˴��ӵ�����h(hu��n)����Ҳ��Ⱦ�˺Ӝϣ��L��������Ҳ�ݱؕ����ʺӘ�(g��u)�����{��
�����ܶ����ӳ����ʮ��ǰ������ˮƽ߀�]�������ǰ��������������������٣���ʹ�У�Ҳ����ƿ�Ӻ��ӡ����b��������֮��S��������˂�����ˮƽ��ߣ������������S֮���࣬�����S��G���������д����ʾ�Ĵ_������
�������Еr���ڴ��������������S��������^�m(x��)���ӡ����������ί�����������x���B������������S�������������T��ԓ�������^�������������߀�ڴ��Љ����N�б��o�h(hu��n)���l(w��i)���������Z�����ǣ����h(hu��n)�����o���R���B(y��ng)�ɣ�߀��Ҫһ���^�̡�
��������ͨ�^���Y̎������
������������Ҫ߀�Ǜ]���X��Ҫ�����X����r���S�ܺ�һЩ�������x���f��֮ǰ�������oÿ��ÿ���l(f��)������Ͱ��߀Ƹ�������h(hu��n)�l(w��i)�ˆT�����T�����ռ���������������������ڴ��ӵ����벻�У��o�h(hu��n)�l(w��i)���Ĺ��Y���������������F(xi��n)��ֻʣ��һ���h(hu��n)�l(w��i)���ˣ�Ŀǰ���@���h(hu��n)�l(w��i)���Ĺ��YҲ�H��200Ԫ��
����ԭ���������������ٶ�����1200���ˣ����ڷN�Nԭ��ԓ��Ľ�(j��ng)�������r�����ã����ÿ�����֧���H�еĎ״������������\���͛]��ʲô�X�ˡ�ԓ����ԇ�Dͨ�^���Y����Q������������}����ɲ���B��ȥ������������@���k���_���˸�����Մ�^�����]Մ�ɡ�
��������������ڬF(xi��n)�����������S���Ļ��A�ϴ�̎�����е��������������ǣ�����������w�����ռ���������k�������Č��������V�����Ͼʹ������@�����^�������x���f��
������(j��)�A�̈�ӛ���˽⣬ԓ��ÿ�����Y���(zh��n)��?li��n)ܵ�ÿ��һ�K�X�ĭh(hu��n)��Ͷ�룬���w��Ҳ��1200��Ԫ�����@�P�X���B֧��ÿ��H�еĎ״��������\�������ã�ʣ�µ�߀��Ҫ�������k���ԻI��
�������sվ����δ����
������ư��������r���ڑ��h�Y���(zh��n)�~կ��ͬ�d�ȴ嶼��ͬ�̶ȵش��ڡ������ڸʺӵĺӵ��У��S��G�����������ĬF(xi��n)�������ˑn�ġ���(j��)�˽⣬��ǰ������ȴ��ӵ�����������Ҫ���\�����ֵ�һ�������������@�����������M�ˣ���һ��ȫ�(zh��n)��ʮ�������������Ҫ�͵��ă����ܶ���Ӷ��]�ס�
�������h�Y���(zh��n)�ǽ��k�Ĺ����ˆT�_����������B�����˽�Q��?sh��)ص����������������ռ����}��ԓ�(zh��n)���ڶ�̖��·��������һ�����ԝM��ȫ�(zh��n)��ʮ����������������ļ����������sվ��������(j��ng)�^���s̎���Ϳ��Լ��r�\����Ҏ(gu��)����������
�����Y���(zh��n)�(zh��n)�L���ʾ��ԓ�������ѽ�(j��ng)���ɣ�ֻ��߀�]��ʹ�ã�����ʽͶ�ú�������������Ͳ����ٰl(f��)���ˡ���
����ӛ��ð������(zh��n)�������f���������Љ��sվ��ԓվ�����~կ�壬λ�ڶ�̖��·��50��һ̎��Ұ�У�����ԓվ�������ϵĴ��T�o�i���܇��ֱ�һȦ����Ȧ���������ܿ���һ����ƶ��ӘǸߵĻ�Ӱ巿�ӵĽ�����Ժ�������������
�������˲�����ǣ��M�ܴ��T�ό�����ֹ���T����������Dz��H�T�����۷x������������Ժ����Ҳ�Ў������y�ѷ������д����f�����ڰ���ǰ���@���������sվ�ͽ����ˣ�Ҳ���˄t�f���ɺÎ����ˣ���ֱ�����ն��]�І��á�
�������_ʼ���ĕr��߀���˓���һ�Σ���������ˣ���һֱ�P���T����֪����Ͷ��Ҫ�ȵ��Εr��ҊЧ������һλ�~կ�����o�εذl(f��)�����}��
 ��ӡ���
��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