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州織錦臺之說
作者:王鈺

2003年4月,天水市政府抽調幾名專家、學者組成一支“天水古民居文物普查小組”,因我是學歷史的,聽到這個消息,很感興趣。利用公休期間,主動征得普查小組的組長祖柄禮、竇建孝的同意,也參與了進來。
“天水古民居文物普查小組”由祖柄禮、竇建孝、李振翼、趙昌榮、王耀 、雷維新、南喜濤、楊凡、牟天生等10多人組成,其主要任務是對天水秦州西關一片古民居進行“拉網式”的普查“定性”,20多天跟隨普查小組專訪、記錄登記、鑒定、整理資料,使我也學到了不少古建筑知識。當普查小組來到育生巷南端和務農巷東端時,普查小組的人大都知道這里有個“織錦臺”。
“織錦臺”,這個名字我從小在鄉下就聽大人說過:“城里有個織錦臺”。還聽過這樣的一句順口溜:“城里有個二郎巷,二郎巷有個古人巷,古人巷有個女兒巷,女兒巷有個織錦臺”。但不知道是啥意思?織錦臺是干啥用的?當進城工作后,又看到了一些資料,才知道是前秦才女蘇蕙織回文詩的地方,可一直沒尋訪過,原因是沒引起多大的興趣。
這次隨古民居普查小組才引起的很大興趣,也感到很驚訝,在中國文學史上有這樣 “濃墨重彩”的一筆,自己忽略了它。尤其驕傲的是我們秦州有這樣的“織錦臺遺址”。
織錦臺遺址處在務農巷的另一條小巷南端,現定為“28號院”,也就是說,從二郎巷走進50米左右,再拐進務農巷的30米,折轉向南的小巷進入約20多米就可到此。二郎巷現為“育生巷”,務農巷原為“古人巷”,二郎巷的小巷多條,只有從東起向西再向南的第二條小巷。
當我們看到:現院內有三間瓦房,屬土木結構的單坡水房,從房屋起架和建筑風格應屬于明代末,靠西南已修建起二層磚混的現代小二樓。那一排單坡水土木房屋,考查人員認為:可能是當年蘇蕙與竇滔居住過的地方,盡管是明代末建筑,但房屋的幾經變遷、歲月的風風雨雨、物換星移,當地人傳承著古人巷的古人故事就在于此地,西南現修建的二層“小洋樓”,據說是蘇蕙織錦的臺基舊址,雖已現代磚混式代替了古老的土木式,可千百年來,人們世代在這里傳頌織錦臺的古老故事。考察組的人員還說:織錦臺不僅局限于這個小院院,過去是這周圍一片,現在住戶院落隔離成這么個樣,但重點是在這個“28號院”。朱炬之先生主編的《天水地名資料匯編》在《織錦臺簡介》一文中載:“千百年來,人們一直把這塊地皮叫它‘織錦臺’,可見在早年一定是有遺址存在的,才能世代相傳下來,不然千百年來,怎能局限地獨稱這一小巷為織錦臺呢?……蘇若蘭驚人的才華,創作了傳頌千古的詩文,就是一千六百年前,在今天水的一個小巷里完成的。清代詩人楊芬燦曾有詩:‘鶯花古巷秦州陌,原是蘇娘舊時宅’。正是指的古人巷的織錦臺遺址了”。
畢業于北京大學文物考古系、曾任天水市文化館館長的竇建孝先生在普查的現場曾對我們說:“今天的‘務農巷’,原稱‘古人巷’,為什么稱‘古人巷’,就是因為前秦的蘇蕙織錦過回文詩,挺有名的,是蘇蕙與竇滔居住過的地方,才稱宅。務農巷是建國后的政治形勢產物,但凡是天水老一輩的城里人都稱它為‘古人巷’,沒人說是‘務農巷’。現28號院,原為16號院,是近年重新登記、重排門牌號的,原16號院為織錦臺遺址之院。解放前這里地址廣闊,路邊有一塊非常光亮的大青石,傳為蘇蕙織錦時的壓機石,近年來因居民修建樓房被埋在樓基下面,織錦臺再也看不到一點遺跡。解放初六十年代,二郎巷口(今育生巷口)西邊還有五間明代所建、二層樓閣式鋪面,鋪面樓檐下懸掛著一塊白底黑字大匾,榜書‘晉竇滔里’四個大字,書法功底深厚,氣勢宏偉,出自明代官宦名人之手。巷口并建有一個面寬兩間牌枋式大門樓,樓檐下懸掛‘古織錦臺’白底黑字大匾,民國四十年代拓展馬路時拆毀。在二郎巷中段靠西的古人巷口(今務農巷口)民國初期還有一個小牌坊,牌坊正中榜書“織錦臺”三字。1920年天水大地震中塌毀,但織錦回文詩歷來人們都十分關注,廣為流傳。詩仙李白曾來過天水,后來在回憶天水的《閨情》詩中寫到:‘織錦心草草,挑燈淚斑斑’。”
世界趙姓文史聯研總會常務副主席、天水玉泉觀文物保護研究所副所長、高級講解員趙昌榮先生說:“1947年我出生在古人巷的鄒家大院,現為42號院,又從小在這條巷子長大成人,這里一直叫‘古人巷’,后來改名了,改務農巷開始人們還不習慣。小時候,出了門,大人問:‘你是哪里住的孩子’?回答是‘古人巷’的。50年代中期,我上解二小學,愛走捷路,經常要路過人們所說的‘織錦臺’院子,那時已沒了院墻,院內土木結構房屋一片,有的房子破破爛爛,有的還閑置著沒人住,人們稱它是古人巷的‘織錦院’,大約有100多平方米,其中有一家姓王的做豆腐生意,我也常去買豆腐。為什么有的房子閑置多,人們說這個院子的房子‘硬’的很,住不住人,只有當官的才能壓住,竇滔是秦州刺史,是大官,所以人家能壓住,但后來也被流放了。記得在我七、八歲時,一天,父親笑著走進門對我說:你看怪不怪,這么一片爛泥的地方,南方人說這地方挺有名的,這個南方的教授,背個照相機,問織錦臺的具體位置,父親指著一處房子說,按人們的說法就在這里,當時居住戶是周昌全,旁邊已蓋起了豬圈,據周家人說蓋豬圈時挖出了幾個柱釘石,有人說那是蘇蕙織錦的繡樓臺基石,這幾個柱釘石說是‘白虎’,養不好豬,就用架子車搬到其他地方丟了。那個教授聽了很惋惜,長長嘆了口氣,在此地連拍了幾張照片就走了。要說‘織錦臺’就知‘古人巷’,要問‘古人巷’就知‘織錦臺’,小時候這兩個名字常常連在一起,據大人們說歷朝歷代就這樣稱呼它,并隔三差五有人走進二郎巷問織錦臺,我也帶過幾回路。
畢業于蘭州大學歷史系、原甘南博物館首任館長李振翼先生生前說:“幼時因與古織錦臺為鄰,加之以傾慕‘鶯花古巷’的詩情畫境之地,再加上孩提時期的好友住在那里,因而我就成了常常造訪這個遺跡地方的常客”。
李振翼還回憶說:作為歷史系畢業生,又是趙儷生教授的得意門生,也師從考古學鄒衡先生的學生,很想為家鄉做點事業,尤其天水的古民居的文物調查和秦州的“五城連珠圖”,曾在50年代中期他就繪制了一幅“五城連珠圖”,圖中標明重點部位,織錦臺就是西城其中重點內容之一,正當他細化五城連珠的具體內容時,一場政治風暴將他卷入“右派行列”,下放在甘南勞動改造去了,從此只留下了“五城連珠”初具模型的大概狀況,細化工作沒完成,因解放初期、中期有相當一部分舊城墻、古民居基本上還沒遭多大破壞,繪制圖標有基礎。比如:現處在天水職業學校校址和育生中學原是西城的城墻舊址,織錦臺就離城墻不遠處。現在的年輕大都不知道吧!平反恢復工作后,當了甘南博物館首任館長,家鄉的“五城連珠”具體量化工作還是沒完成,原因一是工作忙,二是舊址破壞嚴重。
李老又說:織錦臺故宅,以歷千余年,是什么樣子已不可尋,但在上個世紀40年代的舊跡,卻依然可尋,當年的殘垣斷壁,門階花圃相互勾連,花壇頹園草木猶存,石鋪引路隱約可辨,此中的廢井頹欄其跡可尋,此中最顯眼的就是綠苔斑斑、隱約可見的殘碑“織錦臺”三字,雖然殘破,鐫刻之刀工中遺留下來之北朝雄渾書風,依然歷歷在目,暴露于露天之下,富麗剛勁的蓮花瓣柱礎清晰可見一斑,至此使我們依稀看到了當年織錦臺的繡臺閣樓高筑,花木奇卉的深宅大院的仙境。直到上世紀五十年代末期,就連這些殘垣故址也一并被平民小院所替代和淹沒了,唯一可作史鑒的殘碑也不知道哪里去了,我成了“右派”,好不容易請了個假回來,抽空去尋那座殘碑已經不見了,就連進入織錦臺的那塊牌坊乃至消失殆盡。
說起牌坊,在李老的記憶中,可能是在50年代末期拆毀的,它曾高高聳立在育生巷口的那座兩層巷道大門樓。李振翼先生說的很詳細,后來他單獨寫了點資料,我復印存于此保留:
“育生巷口的大門樓,是一座兩坡水懸山頂以木結構為主的過街樓式的古建筑。它跨街連巷而立,粗大的四根檐柱和兩根山柱直立在大型的石礎基上,堅實有力,下層柱頭枋板、闌板齊全,云子雀質樸簡練,古色猶存,為其全巷大通道之總門戶。內側有樓梯可通二層。下設花板牙子勾柵闌干,四扇直隔窗,刻花遍布,玲瓏剔透,質樸大方。檐下透花闌板下有云子雀替,其下十字拱簡約而古樸,有前期明代風貌。二樓屋頂正頂脊蓮花纏枝卷葉為飾,兩端龍吻高聳,壯觀威嚴,不失其古風。屋面筒瓦鋪頂,連菊瓦當勾滴相間,自有一番高雅情趣。二樓內自然是老百姓祈求神佛保佑一方居民平安的最佳選擇之設施。兩廂而供,其中墻壁上繪有神仙壁畫。據說還在其中繪有竇滔和蘇蕙的一段優美的連環圖壁畫故事,可謂神人共慶,天人合一的最佳選擇。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是在門樓二層之上正反兩面均豎有一方木制匾額,臨華嚴前街的巨額匾,其上所書“晉竇滔里”四個如椽之雄建剛勁、滿布于其中氣勢非凡的墨書大字,在街頭遠遠望去,十分顯眼,上下并無款書。在巷內的另一面置于闌干外的那塊“古織錦臺”巨匾,白底黑字雄渾質樸,古拙有加,亦無落款。雖前后的字體有別,制作風格劃一,字跡滿布其間,與當年伏羲廟的過街牌坊榜書如出一轍。
李振翼先生還提供了他的好友敬燕生的一篇文章《我所了解的織錦臺》。“我看過數篇有關織錦臺的文章,一般主要記述蘇蕙織錦的故事,而對織錦臺這一地域的敘述只寥寥數語,一說織錦臺在育生巷南端;一說在縣城西關二郎巷(現育生巷),因為育生巷口原有門樓,樓上供奉著無量祖師,門樓朝街面懸有‘晉竇滔里’匾額,門樓朝巷內面掛有‘古織錦臺’匾額。約在1958年門樓被拆,匾額被育生巷幼兒園當做案板使用毀掉了。確切的說:織錦臺不在二郎巷而在古人巷(“古人就是指蘇蕙而言),即現在務農巷,具體是在育生巷東端有一條向西的長巷,入內約80米,第一條向南的短巷叫‘煙房巷’(有人也稱‘淹坊巷’),再西約20米,第二條短巷即為織錦臺。這一片計有10所院落,據父輩講,古時候的織錦臺在后巷道徐家院,入院東房為庭房,是蘇蕙居住和織錦臺的所在地。解放前,該屋始終未住人,當做徐家的干果庫房。老人們常說:‘這房煞氣硬,住上人總是不太平’!解放后,世道變了,房管局安排了住戶,有的人家請了陰陽‘安頓’,再沒聽說出什么事,這是閑話。由于住戶擴房包了前檐,失去了原建筑風貌,聽鄰居們說:某年江蘇電視臺來采訪,無法拍攝蘇氏住所,故把我家的庭房(坐北朝南,明代建筑)當織錦臺的位置攝入鏡頭走了”。
在“古民居文物普查”中,因28號院只存有明末土木結構單坡水瓦房,周圍一片房屋和院落已變樣,難于定性,只能說“織錦臺”在這周圍一片,28號院應為是重點,因從民間代代傳承默認。李振翼先生現場考察時說:“老一輩天水人從來把古織錦臺即不看成是二郎巷,也不看成是古人巷的一部分,而是將它看做是此兩巷道之間接合部的另一單獨地段,地理學稱‘片地’的古織錦臺地方。已故的天水名中醫王仲青曾說過:‘過去解放前織錦臺院是有名的‘竹子院’。竹子長了大半個院子,安泰堂(中藥店)的人來院摘竹葉、刮竹茹,當時稱徐家大院,也稱竹子院’。”
總的來看織錦臺無論如何,不管怎么說在天水這一點毫無疑問。今年4月,由天水著名作家龐瑞林女士組織蘇蕙文化研究會的同仁赴寶雞扶風、武功等地考察,才知織錦臺還在爭論:有寶雞扶風之說,襄陽之說,昆明之說,使我大吃一驚,十分感到驚訝。過去我們“夜郎自大”,驕傲之處是蘇蕙織錦之地在天水,天水人從來沒有持疑過, 沒想到外面還在“大論戰”。元末明初陶宗儀所編的《說郛》卷七十八文中:“前秦苻堅時,秦州刺史,扶風竇滔妻蘇氏在秦州悔恨自傷,因織回文詩。”《天水市地名資料匯編》:“解放前巷口門樓懸有‘古織錦臺’和‘晉竇滔里’的兩面大字匾額,書法雄健,沒有年月記載,從木質蝕朽面貌來看,可知是幾百年的文物,解放后拆除門樓,一并損毀。寶雞扶風的丁勝源、周漢芳二位在編著的《前秦女詩人蘇蕙研究》一書中,在《﹤璇璣圖﹥的寫作及織錦時間、地點》的篇章中將分歧的地方進行了各自的闡述,但在闡述“天水之說”之中也毫不掩飾的說明了情況,這點可以說是難能可貴的。
天水說:比起扶風來,此說鮮為人知。元代的、戴表元《織錦回文苻堅時秦州刺史竇滔妻蘇若蘭為其夫徙流沙作》,開頭便說:“君不見秦州城中雙蒂花,春風吹散著流沙,流沙千營復萬轉,織入彩機歌不斷。”只有到過秦州的人,才知道這里也有蘇蕙寓處。清吳浩在《蘇蕙故里》:“經行來故里,何處聽吟哦”。乾隆間,秦州知州國梁《織錦圖》詩:“一自若蘭傳錦字,故居今表竇連波”,自注:“甘肅秦州西關有坊曰,‘晉竇滔里’。清扶羌知縣、靈州知州楊芬燦《織錦巷歌》云:鶯花古巷秦州陌,原是蘇娘舊時宅,遺址誰尋灈錦坊,居人尚指支機石”。又李善《文選》注引《織錦回文詩序》有“臨去別蘇”之語,苻堅雖懷婦人之仁,也斷不至于能讓貶謫之臣,先返鄉里告辭家眷,然后再往戌處的吧!因而,這“別蘇”之地,當是任所——秦州。
《【乾隆】直隸秦州新志》卷二故跡:“竇滔故里,在州西郭,有織錦臺”。
《【民國】天水縣志》卷一古蹟:“在縣城西關二郎巷,傳為晉安將軍竇滔妻蘇若蘭織繪文錦之處。”二郎巷今改名育生巷。此巷臨西關大街處原有門樓,正面懸“古織錦臺”匾額,樓后懸“晉竇滔里”匾額,當系明代時遺物。解放初期,駐軍拆樓,兩匾遂不知去向。織錦臺在育生巷中的務農巷內,當地居民把整個務農巷喚做織錦臺的。
蘇蕙《璇璣圖詩》到底織造于何地?李蔚認為以定天水為宜,其理由是:
苻堅時官吏赴任是帶家眷的,蘇蕙自應偕竇滔同往秦州任所。(《【民國】甘肅通志稿》卷九十六,亦謂“滔仕苻堅為秦州刺史,摯蕙之官”);而竇滔謫戌敦煌是由秦州出發的,設想蘇蕙其時被留秦州,當是合理的;竇滔在謫戌中授職安南將軍,命去鎮守襄陽,蘇氏“不與偕行”,自當仍居秦州。據此推測,她是在秦州織就回文錦的。
詩中有“秦西”、“西秦”詞,前秦建都長安,被稱為“西秦”或“秦西”的地方,自不可能為近在咫尺的扶風,而只會是更西向的秦州。詩中自稱“山梁民”,此與天水地處山區的地貌吻合,而與地處關中平原的扶風,在地貌上相差甚遠。又詩中有“休林桃,憩圃桑,流泉清,塵飛揚”,這種自然景象在關中地區很難看到的,相反在天水卻是不斷發生。《扶風縣志》所載,反映的是當地人民對故鄉歷史人物的一種熱愛,并不符合歷史事實本身。
(原發微信《讀寫人家》201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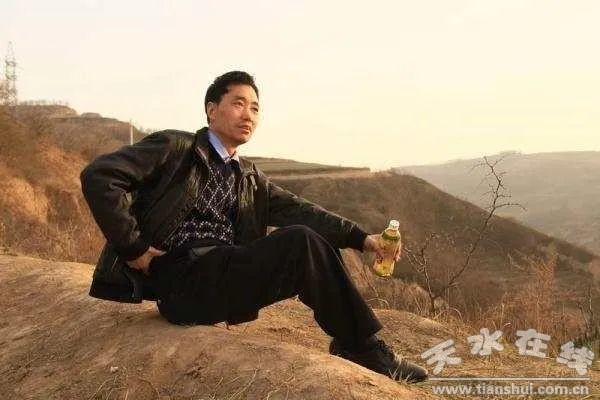
作者簡介
王鈺,筆名覆盆子,甘肅天水市人。出版文集《筆走大墻內外》、長篇紀實小說《25號監舍》、中篇報告文學《難忘的歲月》、發表中篇小說《九花》,主編《神農山與神農文化》,發表論文《青少年紋身初探》、《大學生犯罪心理與矯治對策》、《伏羲、人類監獄發展史的肇啟者》等十多篇。為中國近現代史史料學會、中華伏羲文化研究會、甘肅省作家協會、天水市作協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