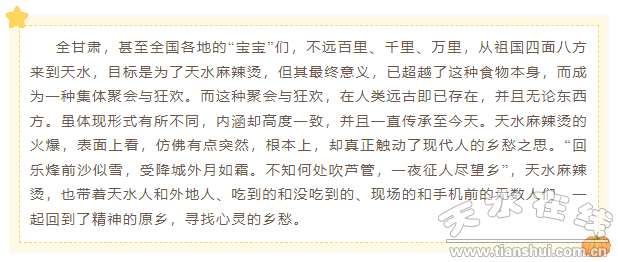

古希臘橄欖豐收時,會舉行奧林匹克運動會,各城邦的人聚集在一起,用運動來慶賀豐收,為勝利者戴上橄欖枝編織的花冠。還會演出戲劇,既有《被縛的普羅米修斯》這樣的悲劇,讓觀眾感受神的無私與偉大,更多的是阿里斯托芬等人創作的喜劇,在觀劇過程中,享受谷物與水果,讓精神與物質共同滿足,更獻給奧林匹斯山上的諸神。不同于今天“三面墻”式的劇場舞臺,古希臘舞臺是圓形的,觀眾在四周,圍著看,且可參與其中。通常只有一個演出者,以獨唱為主,通過演唱與表演,向觀眾講 述故事。因此,當時的戲劇稱作“戲劇詩”。古希臘百科全書式的大學者亞里士多德的文藝學名著《詩學》,就是古希臘戲劇的研究專著。
天水麻辣燙的火爆,直接引來的,是甘肅全省各市州諸多演出形式到天水的風云匯聚。而所有的演出,全在街上,而非秦州大劇院等劇場。演出者,不能稱之為演員,因為不是專門從事這一職業,穿上戲裝,就是演戲者,脫下戲裝,就回歸到本來的職業,或農民、或務工者、或教師、或學生,等等。這與古希臘的演出非常類似。時間上相差三千余年,空間上相距萬余公里,文明演進的階段,差別巨大,但人類的情感需求是相通的。這也正是東西方文明各自發源,但發展階段相一致的根本原因之一。據此,馬克思才提出人類社會五大發展階段這一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

中國戲劇出現較晚,成形態的戲劇,要到宋元時期才有,但戲劇形態的萌芽卻出現甚早,其主要發生形式,便是節日的社火,也是最原始的群眾娛樂活動。但非“娛人”,而重在“娛神”。功能上,與古希臘一致。
節氣是古代中國對于太陽運行規律與農時關系的科學把握。農歷既不是單純以月相變化為基礎的陰歷,也非今天我們標準使用的陽歷,而是陰陽混合歷。以月相變化之一周期為一月,同時,輔以反映太陽在黃道面上運行之關鍵節點的節氣。如今,節氣已成為重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成為中華民族共同鄉愁的重要載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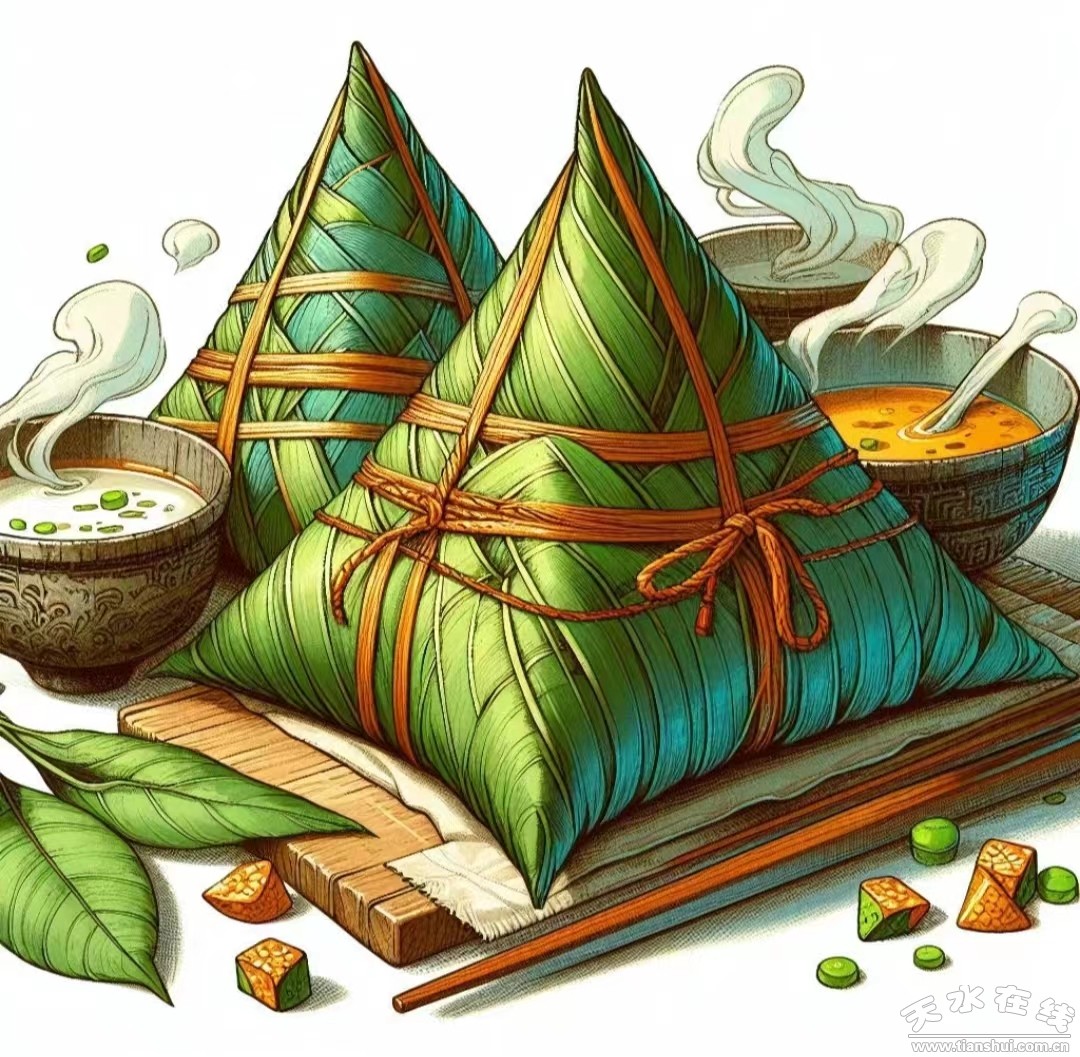
節日,是節氣的簡易記憶。春節是立春的簡易記憶,元宵節是雨水的簡易記憶;二月二龍抬頭,其實是蟲抬頭,指驚蟄;三月三踏青,記憶清明;“端午”之意為正中午時,太陽正在天頂,端午節亦稱端陽節,由此可知,其體現在立夏。六月六吃涼面,因此為一年之最熱者,大暑;“纖云弄巧,飛星傳恨,銀漢迢迢暗度。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牛郎織女七夕相會的美麗傳說,其實質,乃在處暑。中秋節,觀其名,即知為秋之中者,秋分也。其后,十月初一為立冬,臘月初八為小寒,臘月二十三為大寒。“寒極之處春水生”,下一個節日便是春節,立春日,新的一年來臨了。

節日,尤其是一年伊始之春節、元宵節,節慶活動既多又廣,非常熱鬧,并且自古而然。辛棄疾《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有句“佛貍祠下,一片神鴉社鼓”,可知宋時迎春社賽已與今天無異。那么,社火,即集社、紅火,它的功能是什么呢?通常的解釋,是祭祀,孔子云“國之大者,在祀與戎”。然而,中國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宗教,其祀者,均有具體目的與訴求,是為“有求必應”也。但在根本上,中國人更重祖宗而非神靈,神靈,也都具有家庭化的色彩,是家里一個神秘而親切的在場者,如灶神等。那么,春節和元宵節的社火,是祭神,也是自娛,是春天剛剛開始,農事活動開始時,對于節氣的紀念。

天水的春節社火非常豐富,扮戲、高蹺、黑社火、雜耍等等,不一而足。正月初一,將祖宗迎回家中供奉,正月初三送回墳上,遍山香燭繚繞、鞭炮齊鳴,表達著后人對于先人的懷念與尊敬,“慎終追遠”翻譯成今天的話,就是“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正月初九,為上九,到玉泉觀朝圣,順星、燒頭香、插冬青、朝山會,順階而上,直至山頂,祈愿一年平安順利。正月十六,相傳乃伏羲生日,無數的人們,無數天水人與外地人,匯聚到春日方至的中華祖廟,以三牲貢獻于人文始祖之前,暗許心中愿望。而每年6月22日夏至日的國家公祭中華人文始祖太昊伏羲,則把這種文化記憶推到了最高峰。全國政協副主席代表國家出席,并率先祭禮,甘肅省政協主席主持,省長恭讀祭文,祭文以《詩經》為基礎之四字句書就,既述古事,追思伏羲十四大功績,又結合現實,以最新之理念、成就,向先祖報上。臺灣與天水,同時獻祭。來自全國與世界的華人子孫,在此獻上最高的敬意。夏至日公祭伏羲,是國家批準的五大國家級祭典之一,其余四者為陜西黃陵祭黃帝、河南新鄭祭黃帝、湖北隨州祭炎帝、山東曲阜祭孔子。祭祀,其根本乃在尋求民族集體的心理皈依,尋找共同的心靈家園,形象化表達,就是心靈的鄉愁。

端午節,通常以為為紀念愛國詩人屈原而設,其實不然。端午節,南方比北方重視,而最熱烈者,當在長江中游之湖北湖南,《荊楚歲時記》中,所記載者頗多。夏至既至,長江中下游早稻成熟,民眾相約慶祝。依水而居,“水不在深,有龍則靈”,龍為江湖之神,則以龍舟現其身,以新熟之谷為其食,因此有賽龍舟、吃粽子風俗。而且,上海浙江等地,一年四季日日食粽,粽子中包咸肉、蛋黃、竹筍等等,其對端午儀式的繼承,明顯越過北方地區。因此,端午與屈原并無根本聯系,乃為長江中下游地區慶祝早稻豐收的活動。可屈子徘徊江畔,見國人無憂患之心,而只一味慶祝,心中無奈,投汨羅江自盡。毛澤東有詩“屈子當年賦楚騷,手中掘有殺人刀。艾蕭太盛芝蘭少,一躍飛入萬里濤”,屈原生于湖北、逝于湖南,今日之行政區劃,仿佛暗示著屈子精神。秋分日,現定為中國農民豐收節,八月十五祭月、吃月餅瓜果,乃北方地區秋糧收獲后的豐收慶祝。由此可知,端午祭日、祭河,中秋祭月、祭土,共同構成中國豐收慶祝體系。與準備耕耘之春節、元宵社火活動一起,營造出中華民族之文化鄉愁氛圍。由此可知,為何春節、端午、中秋得“佳節”之稱,而其余諸節日無此殊榮。

天水作為中華文化源頭區,華夏第一都城,乃中華文化之長房長孫,文化傳承久遠而正宗。麻辣燙雖為一種小吃,制作簡單而價格便宜,然其蘊含的文化意味,卻非常深厚。民以食為天,伏羲者,“庖犧氏也”,其意即負責做飯和分發食物的人。古時食物匱乏,唯智慧、道德超群服眾之人,方可擔此重任。天水麻辣燙之所以火爆,于物質層面,乃使用中華文明傳承最正宗之地的食材,于文化層面,在“澤被華夏一萬年”的羲里媧鄉,于環境層面,品嘗美食的同時,欣賞著豐富精彩的社火表演。而在本質上,社火,以及中國民間的諸項活動,幾乎無不與食物相關聯。

依天水習俗,正月十六之后,所有社火家什都要放起來,扮戲的衣物燒掉。孔子云“盡人事,知天命”,于民間,則是“知天命,盡人事”,與神同樂或曰“娛神”完畢,便卸裝下田,開始勞作。天水麻辣燙成為熱點后,天水歷史上第一次于正月十六之外,社火重新演起來。不僅全套盡出,而且開發出許多新活動,秦腔劇團等,也紛紛出動。加之甘肅其他十三個市州的助力,幾乎成了隴原“非遺”展演地。然考其實質,依然乃對食物之尊奉也。天水麻辣燙雖僅25元一份,傳承傳遞的,卻是中華文明最之最核心者。社火的“反季節”出現,便不自覺地為這傳承插上了弘揚的翅膀。發掘至最深處,便看到中華民族,乃至全人類共同的鄉愁。

李曉東,中國作家協會社聯部主任,文學博士,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研究方向為明清白話小說、中國現代戲劇、新時期文學,著有散文集《天風水雅》等。曾掛職甘肅省天水市委常委、副市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