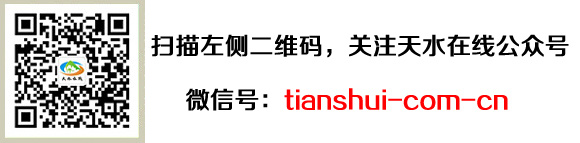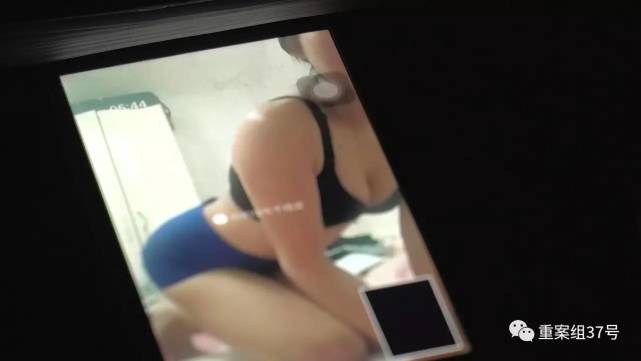2017年4月1日,中央宣布成立雄安新區,主要包括河北雄縣、容城、安新3縣等地,是繼深圳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之后又一具有全國意義的新區。這一消息在京津冀乃至全國“爆炸”開來,牽動人們敏感的神經和“嗅覺”。
如果說,三年來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推進,主要屬于戰術層面的“伐兵”和“攻城”,那也不妨說,河北雄安新區的布局和落子,真正具有了上兵伐謀、以謀取勝的內涵。
規劃中的雄安新區,包括雄縣、容城、安新3縣及周邊部分區域。這個選址和布局,初看起來有些出人意料,但細思之則發現意味深遠。
文| 上海交通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院長、教授劉士林
本文為瞭望智庫原創文章,如需轉載請在文前注明來源瞭望智庫(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則將嚴格追究法律責任
1
戰略定位:既是國家級新區又是國家經濟特區
4月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通知,決定設立河北雄安新區。雄安新區是繼深圳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之后又一具有全國意義的新區,也是繼規劃建設北京城市副中心后又一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歷史性戰略選擇,是千年大計、國家大事。
雄安新區一瞬間街談巷議,網絡、微信迅速刷屏。
雄安新區雖被冠以新區之名,并與浦東新區相并列,但與層級最高的國家級新區明顯不同,一亮相就比同級別的濱海新區、兩江新區、舟山新區等高出許多,因為它同時還與深圳經濟特區并列,因此可以把雄安新區初步界定為:既是國家級新區又是國家經濟特區。
這可能就是在文件中首次使用“千年大計、國家大事”的主要原因。這兩個詞并用,主要是強調茲事重大。但它們又都屬于一種質性界定,不好量化,所以到底重要重大到什么程度,我們只能從中國文化和歷史的角度加以揣度。
關于千年大計,在漢語中最容易使人想到的是“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意思是只有按照自然、社會和文化的規律去做某件事才能成功。關于國家大事,本于《左傳·成公十三年》記載的“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是指“和睦邦族”的祭祀與抵御外辱的戰爭。由這兩方面出發,結合雄安新區的規劃建設,可以這樣理解“千年大計、國家大事”。首先,城建史上有一句話叫“千年風水”,意思是城市選址和空間布局一經確定并開建,就會徹底改變自然環境并很難再回到自然的原初形態,因此城市的規劃與建設比種樹育人更加重要和影響深遠。其次,在《詩經·大雅·緜》中,曾把周人在周原上“乃立冢土”當作西周興國大業完成的標志,這也就是《左傳》講的“祀”或摩爾根講的作為文明社會標志的“禮儀中心”。把這兩方面結合起來,可以推知雄安新區被賦予了怎樣高的期望和怎樣重要的國家職能。
雄安新區是一個新生事物,從雄縣和安新兩縣各取一字,既具大國氣象,又兼備大都風范。十年樹木,可以足用;百年樹人,可以齊家;千年建城,可以安邦。
2
大國大都,需要規劃一個更大的戰略騰挪空間
在最近的朋友圈中流傳著一個提倡睡眠的微信。其實,不僅是快節奏生活的現代人,高速發展的中國城市也早就有了休養生息的強烈需要。
擁有3000多年建城史與800多年建都史的北京,目前中心城區人口超23000人/平方公里,機動車保有量超500萬輛,既有“首堵”之戲稱,又經常陷于“十面霾伏”中,再加上怎么也都治不了的高房價、上學難、看病難等,說明這座大城已經很累、很累、很累了。當一個人累了,最有效的辦法莫過于睡上一大覺。而當一個城市病了,最管用的對策是減去已超過它承載極限的東西。但我們沒有辦法想象,如何給這個超負荷運轉的大都市放假。
一般人都以為雄安新區的設置很突然,其實并不是的。因為像這樣一個國家重大戰略決策,不僅不會輕易做出,還可以說是經歷了很多的投石問路并在巨大現實壓力下才做出的。理解這個問題的關鍵,是如何把相關信息聯系起來。
面對北京日益嚴重的“大城市病”,人們能想的和能做的都已想過和試過,其結果可以“不大勝亦不大敗”一語概之。在“想”的方面,從傳了十幾年的各種版本的遷都說,到不久前仍在小道游走的“即將設置首都特區”等,集中表達的中心思想就是北京已不適合再做首都了;在“試”的方面,從地方上看,如山東省濟寧市早就提出要建文化副都,期望能承擔一部分首都的功能,這事一直鬧到2009年全國兩會才無疾而終。從北京自身看,為了應對城市病也做了很多,其中一大手筆是把首鋼整體搬遷到河北曹妃甸。從國家層面看,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把天津列為雙核心城市之一,也是出于解決北京市“一城獨大”的頑疾,但天津同樣也飽受著大城市病之苦。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2015年7月,北京市提出“聚焦通州,加快北京市行政副中心的規劃建設”,后來又排出到2017年底將政府四套班子搬到通州的計劃,盡管這個動作已不算小,但預計只能疏散出40萬左右人口,這與北京的2000多萬的常住人口相比,作用相當有限。
與此同時,不管北京市怎么提高門檻,外來人口增速仍持續走高。截止到2015年年末,在北京市2170.5萬常住人口中,外來人口高達822.6萬,占比為37.9%。而據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僅2010年河北流入人口就超過北京流動人口總量的五分之一。凡此表明,各種優勢資源過度集中的首都北京的城市磁力過于強大,如果在周邊不能有一個可以和它相媲美的城市,京津冀的協同發展,就極有可能是圍著北京市再攤一個更大的大餅。展眼望去,在京津冀要找一個這樣的地方并不容易,不僅天津和石家莊不行,連地級城市保定的人口也都超過1千萬,再怎么拓展,都不可能建成一個巨大的人口蓄水池。
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提出:必須認識、尊重、順應城市發展規律,端正城市發展指導思想。中外歷史上很多都市的遷移和擴建,都是出于遵從自然規律、協調人和自然矛盾的現實需要。從中國古代都城史的角度看,無論是漢唐的雙都城——長安和洛陽,還是唐代對隋朝都城、元代對北京城的擴建,都是因為舊都不能滿足帝國首都必須具備的城市功能。從西方現代大都市的角度,19世紀下半葉,倫敦、曼徹斯特、紐約、芝加哥等在出現了人口擁擠、環境污染、貧富差距懸殊等“城市病”后,也都不約而同地采取了另建新城的策略。
俗話說,“樹挪死人挪活”,對于一個城市也是如此。在經濟全球化和政治多極化的當今世界,在積極應對北京大城市病的同時,另擇空間建設一個國家副中心,以備不時之需,對于捍衛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是絕對必要的。在某種意義上,就像農業生產中的輪耕制,雄安新區的設置,可以看做是“都城空間輪耕制度”的一次探索,完全符合城市發展的規律。
3
上兵伐謀:一子落定,滿盤皆活
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如果說,三年來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推進,主要屬于戰術層面的“伐兵”和“攻城”,那也不妨說,河北雄安新區的布局和落子,真正具有了上兵伐謀、以謀取勝的內涵。
規劃中的雄安新區,包括雄縣、容城、安新3縣及周邊部分區域。這個選址和布局,初看起來有些出人意料,但細思之則發現意味深遠。
首先,雄安新區一直是交通戰略要地,距北京、天津只有100公里,屬于高速1小時、城際高鐵半小時的交通圈內,此次浮出水面,有望在京津冀腹地形成一個新的“中心地”。
其次,城市化水平較低,新區內人力資源、土地資源相對充足,坐擁華北平原最大的淡水湖泊——白洋淀,擁有良好的發展潛力和市場空間,還可連帶解決京津冀區域的“中部塌陷”問題。
再次,遠期規劃面積2000平方公里,比深圳經濟特區(1990平方公里)略大,不到浦東新區(1200平方公里)的兩倍,建成后可容納人口超過1000萬,這樣的規模和體量足以為解決京津冀協調發展的核心問題——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提供輾轉騰挪的戰略空間,且與其他地方相比,三個縣城的建設成本又是最低的。
最后,具有一子落定滿盤皆活的系統效應。比較而言,在一窮二白上,雄安新區有些像當年的小漁村深圳,在后發優勢上,又像當年和滬西一江之隔的浦東,前者深入到戰略前沿,后者具備雄厚的外勢。在沒有這個新區時,誰也看不出京津冀與一帶一路、長江經濟帶如何互動,而一旦有了這個新區,一幅“南深圳,東浦東,北雄安”的深化改革和開放發展宏圖已躍然紙上。
在戰略一詞已被用濫的當下,這才是真正的城市戰略規劃。不同于一般的空間、人口、交通、土地、金融、文旅等專項規劃,它既在橫向上統籌了環境、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發展要素及其交互作用關系,又要在縱向上把握過去、當下、未來的內在關聯及其包含的風險和機遇,是一種更加系統的國家大局設計和一種前瞻性的千年城市謀劃。
當然,“羅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雄安新區的規劃才剛剛邁出第一步。由于涉及環境資源、人口、經濟、社會、文化等多要素,以及體量巨大、關系眾多和層級復雜等原因,不論是規劃剛剛提出的現階段,還是在以后的規劃建設進程中,出現一些懷疑、搖擺、反復甚至是局部的困難,可以說都是正常和無可避免的,對此既無須“大驚小怪”,也要防止“因噎廢食”。對于所有“發展中的問題”,只能以更高水平的發展去解決。
 打印本頁
打印本頁